5月19日,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(CSIS)发布“链接国家安全与创新基础”系列研究的第二份报告《绘制国家安全工业基础:政策制定》,概述了国家安全工业基础(NSIB)的要素构成和运行、发展历程,重点审视了商业创新模式与国防技术发展的差异,探索大国竞争环境下,更好利用国家创新基础响应国家安全需求的政策方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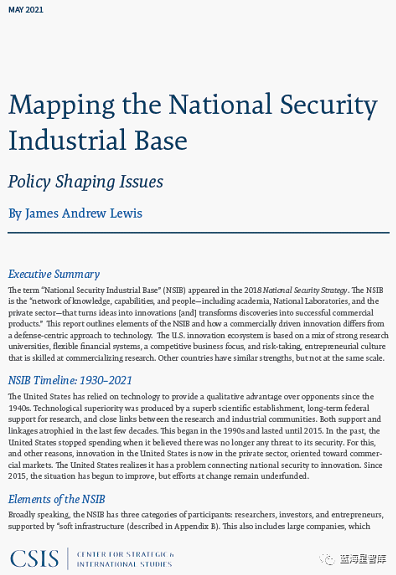
图1 报告封面
一、国家安全工业基础的概念和历史发展
报告套用美国2017年《国家安全战略》中“国家安全创新基础”的概念(两者英文简称均为NSIB),来界定其核心概念“国家安全工业基础”,进而将焦点集中在科技开发和创新上。
(一)国家安全工业基础的概念分析
1、概念辨析
与“国防工业基础”概念相比,“国家安全工业基础”的含义更宽泛,将国家安全的概念从军事能力和国防工业扩展到“包括更广泛的经济和技术重点”,更贴合当前大国竞争的形势。
与“国家创新生态体系”相比,“国家创新生态体系”更聚焦于私营部门出于商业目的而进行的技术开发和应用,但鉴于其中很多技术具有军事价值,在服务于国家安全需求时,其即为“国家安全工业基础”。不过报告自身也未严格区分使用这两个措辞。
2、要素构成
广义的国家安全工业基础的参与方有三类:研究机构、投资方和企业,这些都是服务国家安全需求的必要基础条件。
强大的研究型大学。美国共有945所研究型大学,根据排名,其中的219所具有高水平研究能力。大学掌握着美联邦约55%的研究资金,并积极参与联邦资助研发中心、各军种研究实验室、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等的研究项目。
灵活的金融体系。美国拥有约1000家风险投资公司,此外还有927家公司拥有风险投资部门。美国共有四分之三的财富百强企业进行了风险投资,且更多企业正逐渐青睐通过投资初创企业来获得创新能力和成果。
大型科技企业重新兴起。大型企业的实验室的数量和作用不断走低,如二十世纪末领导美国基础研究的IBM研究实验室和贝尔实验室。但围绕人工智能、量子等新兴领域的大型科技企业重新兴起,航空航天、生物制药、计算机、科学仪器、半导体和通信设备等行业研发投入巨大,开始成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的核心。

图2 已被诺基亚收购的贝尔实验室
国防承包商做出贡献。这些承包商既包括大型军工企业,如洛马公司的臭鼬工厂,也包括中小型企业,这些企业通过提供大量工程技术人才、组件研究团队等方式,为国家安全创新做出重要贡献。正如2017年版《国家安全战略》指出,“国防工业基础”是“美国国家实力和国家安全创新基础的一个关键要素”。
科技人才队伍强大但在某些技术领域存在短缺。报告指出,美国吸引着大量优秀移民,且是全世界研究生教育最具吸引力的国家,但在某些技术领域仍长期存在人才匮乏问题。
3、软实力
报告认为,国家创新生态体系的运行效果取决于“无形因素”,即“软基础设施”,包括文化、教育、金融、商务、法律等。其中最为关键的,是业务运行相关法律规章、知识产权保护举措、资本市场支持等的相互协调和支撑。报告认为美国的“软基础设施”是美国创新生态体系的优势之一,其重要性堪比硬基础设施和研究支出。
(二)国家安全工业基础的历史发展
报告回顾了从上世纪30年代至今,美国国家安全工业基础的发展脉络。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:
上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,美国有着“优秀的科学机构,持续、长期的联邦研究支持,以及研究机构和工业界之间的密切联系”。如30年代联邦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,二战期间组建国防研究委员会等机构并成功实施曼哈顿计划,冷战期间成立各军种研究机构,大力发展精确制导、隐身、传感器等技术。
上世纪90年代至2015年,美国在国家安全创新方面维持“长达25年的漠不关心”,缺乏对竞争对手的关注,资金支持不足,秉持不利于创新的规避风险型文化。
2015年以来,美国开始通过新机制来扭转规避风险型文化,积极引入商业力量和成果。如成立国防创新小组、空军创新工场等,但在创新方面“下大赌注”的步伐还不够快,“国家安全的大部分研发支出仍在传统渠道”。

图3 空军创新工场标志
二、国家创新基础与国家安全需求之间的矛盾
报告分析了商业利益驱动下,国家创新基础运行与满足国家安全需求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和鸿沟,以明确政策取向,使国家创新基础更多服务于国家安全工业基础建设。
一是国防部门不了解国家创新市场。国防部应侧重识别而不是“定制”可用于国家安全目的的商业技术,才能更好获得创新机遇。但是目前除了国防创新小组、创新工场的尝试,国防部还不能有效识别、投资和采办市场上可满足国防需求的商业技术。
二是国防部和商业界对风险和利益的认知存在差异。国防采办注重需求明确、流程规范、进度可控,而商业企业、风险投资公司不喜欢这些繁文缛节,宁肯冒更大风险和不确定性来追求更高利益。
三是对创新效力的评价标准不可确定。报告认为传统的专利、论文数量等评价标准有失科学和客观,而“收入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衡量标准”——企业用营收,国家用国民收入总值。但报告也指出,收入标准有其局限性,并且如果政府的投入缺乏探索精神,就可能得不到充分的回报。
基于以上考虑,报告提出了链接国家安全需求与国家创新基础的文化和激励政策。其前提认识是,创新是分布式的,参与者成千上万,因此需要将国家安全工业基础的创新视为一个“市场”,而不是完全采取自上而下的计划指令。这其中需要政府借力于激励和导向的变化,告知投资方和企业,国家在安全领域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在哪里。
三、与中国的对比
报告对中美两国国家安全创新体系进行了对比,总体认为中国国家创新基础的生产力弱于美国,但链接创新基础与国家安全需求的能力是中国的优势。
在管理方面,报告认为中国的创新基础管理模式为“国家/市场混合型”。报告指出中国的优势在于“一直有意愿投资于科学和技术基础”,并越来越多地将投资聚焦于战略目标,确保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得以持续,结束技术对外依赖,建设一个能自主生产高技术武器装备和商业产品的创新基础。但报告同时认为过多地以政策取代市场会“使创新放缓或后退”;同时认为研究和创新是国际属性的,“以国际为中心”的美国,会比“以国家为中心”的中国在技术领导地位上更具竞争力。
在创新基础方面,报告认为美国的风险投资和研究型大学“优势更加突出”。报告称中国风险投资经历了10年的繁荣发展,但2019年后因为中美贸易战和缺乏商业吸引力等原因出现“衰退”;中国的科技人才队伍数量具有绝对优势但质量不如美国;中国大学数量多,但缺乏顶尖水平的大学;基础研究投入高但因基础薄弱,可能会影响投入收益。与中国相比,美国的优势在于创业精神和创新基础,即擅长研究和转化,而中国创新基础薄弱,但创业能力很强劲。
在服务国家安全方面,报告认为中国对“民用技术和国防技术的生态体系进行了深度整合”,国家安全成为国家创新的驱动器。报告还指出,中国政府所属研究中心在国家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,越来越多的民口大学在参与军事研究。但报告也点出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,认为中国与美国科技公司一样面临着程序上的一些阻力。
在科技发展方面,报告认为美国基础能力具有固有优势,但中国的优势和发展不容小觑。中国已经在量子加密、人工智能、自动驾驶和生物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;中国还引领了数字货币的发展并从其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中得益;中国有强大的“应用程序”经济,能够充分利用移动设备提供金融科技和软件产品。美国在半导体、软件、5G和6G方面领先,在人工智能、量子和生物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较小;中国在半导体制造设备和先进芯片方面依赖美国。
四、政策取向建议
报告认为,国家安全要更好地利用以私营部门为主体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,寻求从合理的机构、资金和机制入手,以获得大国竞争优势。
一是构建新型合作伙伴关系。扩大与“发明家和企业家”的伙伴关系,以及与欧洲和亚洲盟友的伙伴关系;推动面向私营部门实施新的激励措施、采取更灵活的机制、建立更宽松的文化,构建国家安全与创新基础之间的新的关系。
二是加大对国家安全工业基础的支持和保障。报告将当前创新乏力归咎于上世纪90年代后对战略竞争对手的缺乏关注,以及由此导致的资金不足和规避风险型文化,因而导致“战略失误”。对此,报告认为加大技术投资和完善创新生态体系,是亡羊补牢的当务之急。
作者:穆玉苹